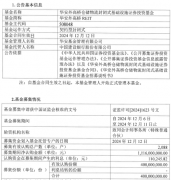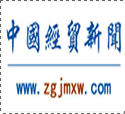北仑的公路上,集卡车像流动的坐标。
超3万名集卡司机,超2.5万辆集卡车,平均周工作时长50.27小时。
每天,数以万计的集卡司机握着方向盘,为生活而奔波。他们是北仑这个世界大港的物流“毛细血管”,也是这座港口城市中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提柜、装货、卸货、还柜。
这四个词串起了他们生活的轨迹。
许宁就生活在这车辙痕之上。
早上5点45分,横浦停车场。许宁打开车门,把水壶、饭盒往车里放,开始检查车况。绕车身,敲轮胎。
他跑省内短线,方向盘转够十小时,多半能回到停车场。
但也有例外。
“前些日子,我在外面待了两天才回来。没办法,工厂说柜子有味道,不给装。洗了,晾了,还是不行。”许宁直起身,额头上的汗珠砸在布满灰尘的裤腿上,路上的日子总归不可能是永远顺利。
在北仑的3万名集卡司机中,安徽、河南和山东人,占了三分之二。许宁今年32岁,是一名退伍军人,来自山东济宁,北仑的集卡师傅中有不少他的老乡。六年前他跟随父亲来到北仑,开始了“上阵父子兵”的传奇生活。现在,父子俩的生活都系在方向盘上。
采访中,记者提出坐坐他的车,许宁欣然应许。集卡车的车头比较高,记者在他的托举下才爬上了车,回头伸手拉他,竟被他拒绝。
“不用,跟我爸学了这么久了,闭着眼都能摸对地方。”
“你们平时会走高速吗?”
“走高速?一公里一块多,绕国道多踩两脚油门的事。”他拍了拍方向盘,“学开集卡的第一节课,就是算这笔账。”
驾驶室里堆着半箱矿泉水,瓶身上凝结的水珠顺着箱底往下淌。“跑国道省过路费,但服务区少,水得备足。”
他说省下来的每一分,都是给家里添的底气。“等攒够了,就和我爸换辆新车,跑起来更稳当。”
张用也来自山东,他的车就停在不远处。
透过车窗,一张全家福被风掀起边角。
与许宁不同,张用的车基本不出市,只在市里转驳箱子。
他说,在码头与堆场间转了十七八年,这条路闭着眼睛都能开了。“提了箱到堆场卸掉,再上码头装箱,多的话一天跑十多趟,少的话五六趟。”
驳空箱时,大部分时间都耗在“等”上面,“早晨上车到晚上收车,全在车上。”
等待是集卡司机的必修课,有人等货,有人等时间,有人等一个平安的消息。
“脑袋里一定要想着法规,别存侥幸心理,平平安安最重要,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平安钱……”他没再说下去,只是握紧了方向盘,目光落在了全家福上。
日子久了,驾驶室里的物件都会沾上人味,磨得越久,反倒越清晰。照片如此,常伴身边的物件也是如此。
郑玉荣是为数不多的女司机之一,她的车刚停稳没多久,挡风玻璃下的红辣椒还在随着惯性轻轻摆动。
“这个辣椒是?”
“下饭吃的,我每次出车都会备着点。”
仪表盘上的北斗系统跳动着时间数字,显示已休息14分钟。
记者问,现在能动一下车吗?
郑玉荣马上说,“挪不了啊!连续开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,挪一步都得重新算!”
“我和丈夫各开一台车,联系基本全靠电话,现在也习惯这种生活了。”
聚少离多是郑玉荣一家人的生活常态,他们的感情都藏在里程里,你多跑一公里,我少歇一分钟。
“很多人感到很惊讶,说你这做事比男人还猛啊,你每天跑这么远呢,我们都受不了。”
“想家人吗?”
“哪有不想的,一年四季我们都很少回湖北老家,包括我的孙子,我一天都没带过,只能在经济上多支持一点。我想着再跑半年就歇一阵,好好听孙子喊句‘奶奶’。”
“不过他们也能体谅我们。”郑玉荣说。
太阳已上三竿,横浦停车场内数百辆集卡车的影子渐渐变短,直到与车子重叠。
从高空俯瞰,一辆辆集卡就像一块块五彩缤纷的砖,砌墙垒房的那种砖。
许宁计算的是每一公里的账,张用稀罕的是那张全家福照片,郑玉荣的车里红辣椒晃啊晃。
这些,都让方向盘上的日子,有了重量。
他们的生活就像集装箱,看着硬邦邦,打开了才知道,里面装着的,全是盼头。(记者 姚 微 谢俊杰)

 手机阅读分享话题
手机阅读分享话题